
切格瓦拉的启示——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
“要时时刻刻提倡读书,努力选择好书籍,使大家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,要逐渐协助新兵接触文化,关心国家大事。学员内心逐步产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围客观形势的逼迫,都能推动学员们由浅入深地去阅读书刊。
——切格瓦拉《游击战》第三章
“影响我们的书?那就是切格瓦拉的《游击战》。”
绑起一头长卷发的兹克里拉曼(Zikri Rahman),身穿黑色上衣,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魄力。
图:苏颖欣

他是“街头书坊”(Buku Jalanan)的创办人之一,当时还是玛拉工艺大学(UiTM)的学生。2011年至今,从沙亚南起家的街头书坊已遍布全球80余个据点。
兹克里不仅活跃于街头书坊,他也是“文学之城”(Literacity)的创办人,以文学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;同时,他也加入了大马左翼联盟,目前他们在积极草拟大选宣言。
兹克里参与的活动当然不止这些,他仿佛对任何议题都有兴趣,常在街头示威、声援活动、文艺活动或讲座上碰见他。毫不夸张地说,他走到哪都会碰见几个相识的人,互相寒暄一阵。
他有时身穿抢眼的蓝色夏威夷衬衫,背着一个印有已故马来作家沙古伯(Pak Sako,原名Ishak Muhammad)头像的袋子。再过两个月,他就要到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硕士班就读。想象新竹街头多了一个颇为嬉皮的马来青年,那画面也蛮有趣。
“我想要更了解东亚。老实说,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吸引我去的,我什么都不懂,就只是想要跳进一个全新的环境,在里面畅游。”
“我也听说,那里有蛮多学者社运人(scholar-activist),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。”
切格瓦拉的启示
斋戒月的一天,和兹克里约了一起开斋,我这时才知道街头书坊除了是2011年全球占领运动浪潮下的产物,原来和古巴革命有些关系。
“我们的策略大多来自切格瓦拉的《游击战》。”
兹克里说,切格瓦拉的战斗手册强调书籍的重要,各个士兵战斗时须带上一本书,读完了再互相交换。
“这有点像流动图书馆的概念,我们就在思考,如何以没有良好组织架构的方式赢得战争?我们虽然小,但其实可以战胜国家,可在学生之中留下一些另类想象。”
“切格瓦拉非常激进,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将理论付诸行动,阅读之后如何从书中吸取东西。”
他声称,理论和实践并非二元对立,而是相互并行。
于是,兹克里和友人们在保守的玛拉工艺大学外,建立起了“街头书坊”,以书籍交换和阅读为策略,作为介入“政治”的管道。
他们奉行“BACA”信念(马来语‘阅读’之意),也是书籍(Books)、艺术(Arts)、文化(Culture)和活跃分子(Activism)的英文缩写。
Buku Jalanan

这就让街头书坊和一般读书会或书友会不同,也让它不仅是学生活动而已。
“一些喜欢文学的人来参加,谈着谈着,就扯到人权议题。我们是文学组织吗?还是社运组织呢?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。”
“我们(街头书坊)是一个混合体……不过,作为一个没有结构的主体也是好的,像一个开放的平台。”
寄宿中学的政治启蒙
兹克里在1990年出生于吉隆坡,也在此长大,而父母则来自吉兰丹。他的三个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,他也在玛拉就读工料测量系,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工程师,才决定于2015年离职,全心投入社运和文化工作。
兹克里在吉兰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师,也是诗人画家,对他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。
“祖父的家有很多书,他什么都读,也刻版画。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伦敦接受教育的教师。”
若要说他的“政治启蒙”时期,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(Kubang Pasu)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。那是他第一次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。
当时,有不少来自华玲和锡县(Sik)的同学,向他谈起70年代的华玲农民抗争。
而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阅报,如《新海峡时报》和《前锋报》,同学之间则私下传阅家长提供的《哈拉卡》或《公正报》这些在野党报纸。
为何要读禁书?
兹克里说,一次沙亚南街头书坊活动,有人带了前马共女战士珊西娅法姬(Shamsiah Fakeh)的回忆录,就有出席者质疑为何要读马共的书,难道不是禁书吗?
事实上,珊西娅的这本回忆录最初是由国民大学(UKM)出版的,已是研究马共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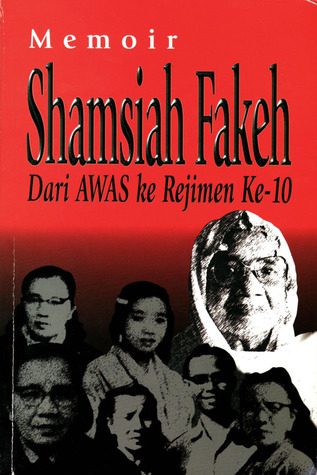
兹克里说,政府的确禁止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马共相关书籍。而街头书坊曾经办过一次“禁书展”,把内政部的禁书封面列印出来展览,以表抗议。这包括重要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(Kahlil Gibran)的《先知》。
兹克里说,从内政部网页上查询,政府自60年代以来查禁的书籍共有逾1600本,其中可看出禁书题材的趋势——6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多,其中包括许多中文书刊;70、80年代则以宗教题材居多;90年代至今仍有许多宗教相关书籍被禁,而有关性内容的书籍也被禁不少。
目前,内政部禁书尤以马来语书籍最多。兹克里认为,马来语是被政治化的语言,而他们要重夺公民对马来语的话语权,因此街头书坊的媒介语皆是马来语。
作为抗争语言的马来语
街头书坊策略性地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言,原因有二:第一,让马来语成为抗争语言,直接和当权者对话;第二,让马来语成为知识语言,但这和“国家文化政策”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却有所不同。
兹克里指出,在马来媒体中几乎没有“抵抗叙述”,大部分人阅读《Kosmo!》或《马来前锋报》等亲政府报章;而一些较批判性的媒体如《商业电台》(BFM)则以英语为媒介,一定程度上能避开政府的监视。
因此,街头书坊试图打开空间,让马来语成为抗争的语言,可以用来谈论被视为“敏感”的课题。他指出,虽然许多人认为沙亚南是较保守的区域,但沙亚南街头书坊至今从未面对什么阻碍。
然而,森州波德申的街头书坊,曾因公开讨论什叶派课题,而遭宗教当局查禁。不同的地理空间,似乎也有不同的“言论自由”标准。
Buku Jalanan

另一方面,马来语要如何成为知识语言?街头书坊在2011年成立之时,是少数使用马来语做知识讨论的团体。
“自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后,国家语文出版局(DBP)要规范我们说话用语的方式,而我们可否跨越这样的界限?”
“2008政治海啸后,‘后烈火莫熄’世代崛起,我们要重夺语言的本质,让它更具世界主义特质,邀请更多人使用它来传播知识。”
因此,不少街头书坊成员在2015年协力举办“Idearaya Festival”,标榜作为批判性的知识和文化平台,全场活动以马来语进行,讨论文化、政治、知识、历史和哲学课题。
他们目前也在筹备着第二届的Idearaya,冀望将知识“下放”至民间,重夺民众对知识、文化和语言的话语权。
马来文化革新运动
这些年来,兹克里和许多马来青年试图以文化运动介入政治,改变社会。而马来独立出版社的蓬勃发展, 更掀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。
这些反叛、不安分的“小集团”,积极对抗国家霸权,也成功“K.O.”掉了国家语文出版局。虽然国家语文出版局将这些马来文学视为“低俗”,但如今人人手上都捧着独立出版的书籍或杂志,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国家机器。
图:苏颖欣

兹克里(见图)认为,文学和文化是互动和介入社会的管道,而马来文学界内部在80年代以后就没有引领文化思辨的论战,以致让人认为保守无趣。
“上一次在马来文学圈的论战,已是80年代的事,是国家文学家沙农阿末(Shahnon Ahmad)和左翼作家卡欣阿末(Kassim Ahmad)针对文学如何符合伊斯兰的争论。”
“沙农认为书写是上苍赋予的任务和责任,而卡欣则认为伊斯兰价值能从任何世俗文本获取。对我而言,这场论战很无趣,而且只局限在马来社群。”
“这样的论战还有关系吗?我们如何往前走,再创造新的论战?事实上,无论在文化、文学或戏剧圈,目前并没有任何论战发生。”
没有形体的文化运动
不过,兹克里对当代的马来独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,并非一味吹捧。
“我有存疑,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(没有论述和回应)……例如我们应如何破除枷锁,干预出版机制的问题。”
“我们应该挑起论战,扣问事情,直接批评……以撼动体制。”
他也指出,一些独立出版社行销书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,有些只是顺应潮流,并没有实质的内容,流于表面。
兹克里认为,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,事情和运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。然而,却有必要去反思和论述这些运动的形成意义,以捕捉当中的精髓。
“这样我们才能将种子撒在各处。街头书坊就像颗种子,有些东西会从中生长。”
Buku Jalanan

他说,街头书坊没有固定的结构样板,却不知不觉“开枝散叶”。
他举例,印尼1998年改革时期以前,就有一些“无形”的文化组织(organisasi tanpa bentuk)。他们不如劳工或妇女组织般有清楚的定位,因此“无形”,却能更自在地和各领域合作串联。
“或许那就是本地文化运动的未来。必须先有文化运动,而之后政治才会跟上。”
也因此,他自认是个如此实践的文化工作者。
新世代的马来青年
兹克里说,由于他在马来社群长大,念的是国立学校,因此在上大学以前,没有一个华人朋友。我好奇地问,难道他在玛拉念书时认识了华裔学生?
“当然不是,玛拉是土著大学嘛。我的华裔朋友都是在街头认识的。”
“是通过社运场合,让我认识华裔朋友。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时代印记,净选盟和其他集会让我们更了解彼此。”
谈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以后的新经济政策,兹克里坦言,当然支持扶弱政策,但不该局限在单一种族,而是给有需要的人。
“我支持玛拉工艺大学向全民开放。”
图:苏颖欣

他说,身为马来人,并不和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冲突。而他并不喜欢强调自己的某些单一身份。
“我们可否有不同的身份认同?可否超越国家强加的身份?”
而他相信,这些身份随时可以置换、改变、更新。
或许,这也是如街头书坊这些“无形”文化运动的精髓,可以自在穿梭于缝隙,也可填补裂缝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