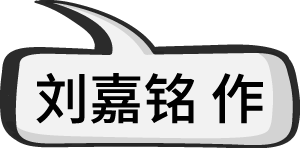千万奖金电竞梦
胜负就在一瞬间,全球数千万人屏息以待,这一场大战将决定谁会出线,进入败者组决赛,挑战世界之巅。
四个马来西亚人加一个菲律宾人坐在电脑荧幕前,手指在键盘与滑鼠上快速飞舞,每一下敲动都化为荧幕上英雄的攻防动作。
只见一名紫色无脸人祭出时间结界,封锁住一队盔甲骑士。但电光石火之间,大地崩裂,盔甲骑士脱困后击杀眼前强敌,并挥军攻入敌方地盘,最终锁定胜局。
这一幕也宣告,由马菲选手组成的Fnatic战队在“2016年刀塔2国际邀请赛”(The International,简称TI)的征途就此终结。
不过,第4名的佳绩,却也意味着Fnatic战队获得145万3932美元(581万5728令吉)进账。即便经过美国政府扣税及战队抽佣,5名队员还是可以均分87万2359美元(348万9436令吉),每个人顿时晋身富豪之列。
打从2011年首届赛事起,刀塔2国际邀请赛的奖金一直位居全球电竞赛事之冠。
去年8月举行的第6届国际邀请赛网络收视率近1亿5000万人次,总奖金高达逾2077万美元,再破纪录。刀塔2玩家更把国际邀请赛的竞技水平,对比为足球运动的世界杯。

不再是废青癖好
对于许多人而言,电玩已不再是“废青的癖好”,而是一个竞技项目。这也是电子竞技(e-sports)一词的由来。选手日以继夜地训练,世界品牌竞相赞助,支持者购票到体育馆捧场,电竞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一门产业。
现年22岁的亚当(Adam Erwann Shah)是个大专生,在雪州世纪大学修读心理学系。他身材高大,穿着随性,打扮与时下年青人无异。
但在刀塔的世界,亚当是名为343的著名选手,职业生涯累计奖金已破百万令吉。在去年8月里约奥运会期间,正当许多人关注马来西亚健儿在奥运舞台的表现时,亚当则作为Fnatic战队的一员,在美国西雅图的Key Arena体育馆追逐梦想,最终与他的队友捧殿军而归。
据esportsearnings.com统计,亚当迄今赢获的奖金达到35万7158美元63美元(142万8634令吉52仙),位居大马电竞选手第5名。
奖金收入榜上,前面13人全是《刀塔2》的选手,接下来才有《反恐精英》、《FIFA 16》与《英雄联盟》等游戏的选手。不过,与前排选手六位数奖金的收入相比,末端选手的奖金收入不可企及。

选手生活有规律
亚当(见图)是在11岁那年,经由死党介绍认识《刀塔》这款游戏,从此就欲罢不能。
不过,当兴趣变成职业,就连亚当也吃不消。他告诉《当今大马》,在去年8月份的TI邀请赛结束后,他根本不想触碰《刀塔》。
“打完TI回来后,我完全不想碰《刀塔》,只想远离它。我想做些之前无法做的事情,我要找朋友,我要去嘛嘛档。”
在TI邀请赛后,Fnatic战队几经重组,当时拿下殿军的阵容已四散。亚当在TI邀请赛后休息了一段时间,并辗转替一些队伍打过替补,包括在11月加盟菲律宾战队Execration,并协助Execration取得波斯顿特锦赛资格。最近,亚当则加入了欧洲战队B)ears。
目前,亚当已申请休学,以专注他的电竞职业。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,顶尖电竞选手的生活很有规律。亚当说,当他还在Fnatic时,全队住在雪州一间独立式洋房,训练屋不仅设备完善,还配有厨师。
“每天早上我们下楼后,就吃早餐和交流,看比赛,或打比赛。只有《刀塔》,你不会上面子书或做些其他的事情,你的电脑荧幕上只有《刀塔》。”
“通常我们会在下午1或2点训练,大概一天会打上两轮三盘两胜的比赛。中间休息时段,可能我们会去游泳或健身一小时半。”
大马五大电竞选手
和他们赢获的奖金(美金)
Chai Yee Fung a.k.a Mushi
Wong Hock Chuan
Khoo Chong Xin a.k.a Ohaiyo
Yeik Nai Zheng a.k. Midone
Adam Erwann Shah a.k.a 343
军训与家人鼓励
到了晚上,亚当与队友又会开始训练打比赛。他强调,要应付如此密集的训练,他们必须要做些运动,否则将应付不来。
更甚的是,亚当说,Fnatic队员当时没有周假,几乎一周训练7天。
“当然,如果有人要出席家庭聚餐,或有人过生日,我们就会衡量状况,然后让他们休假出外。”
虽然军训式的生活异常疲累,但亚当表示,电竞选手可以到多个国家参加比赛,看到许多新鲜事物,感觉就像是种补偿。
一连紧凑训练中,亚当尽量抽空陪伴女友家人。有时候,从国外比赛回国后,选手们会获得两三天休假,而亚当则格外珍惜难得的假期,与女友及家人窝在一起。
庆幸的是,亚当的女友与家人相当支持他投入电竞职业,就连他84岁的外婆也通过电视直播,观看他打比赛。
“每逢大赛的时候,全家人都会一起看电视。虽然他们看得不是很懂,但也会在电视机前大声喊加油……我觉得这特别感动,因为你会知道,如果你输的话,你就让他们失望。”
“这就像是一种勉励,会让你更加努力。”
打游戏算运动吗?
跟亚当家人的开通相比,18岁新秀杨明健(《刀塔2》网名Syeonix)则费了一番努力,才说服父母让他成为电竞选手。
杨明健(图中右者)来自吉隆坡的小康之家。他的父亲杨富才现年61岁,从事消防用具生意。他一开始并不认同幼子杨明健全职投入电竞行业,更指“打机”浪费时间。
杨富才与妻子黄珊珊都热爱运动,分别喜爱壁球与高尔夫。黄珊珊说,与其让儿子打电动,不如挥杆打高尔夫更好。
杨富才则认为,电子竞技根本就不算是运动。
“我不认为电子竞技是运动……你只是坐在电脑前,能够锻炼身体吗?打游戏是运动吗?”
杨富才的想法一直没变,唯一改变的是,他如今不反对儿子当一名电竞选手。至于改变的契机,则是因为2015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马来西亚电竞赛(Malaysia Cyber Games)。
当时,主办单位邀请首相纳吉与通讯部长沙烈赛益担任特别嘉宾,为得奖者颁奖。纳吉与电竞赛事扯上关系,虽然引起刀塔圈子反弹,但却说服杨富才支持孩子投入电竞领域。
杨富才笑着说:“连青体部都办电竞大赛,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有前途。连阿Jib哥都出席,有前途,有前途。”
联名户口存奖金
在这之后,杨明健父母不仅让儿子展开全职电竞选手生涯,更给予许多支持与协助。黄珊珊即为儿子购置全套的高阶电脑,好让儿子能在家中训练。她也与杨明健开设联名银行户口,共同管理杨明健所赚取的奖金与薪金。
杨明健在去年3月加盟号称为大马国家队的“虎牙队”(Taring)。当时,他享有4000令吉的月薪,但却须南下柔佛,跟队友住在新山的训练屋。
当时,杨明健刚完成中学学业,取得大马教育文凭。在新山集训期间,杨明健感染骨痛热症,恰巧碰到刀塔2国际邀请赛东南亚入选赛前一周。
由于杨明健高烧不退,他的父母连夜驱车南下,探望瘦削的幼子。虽然身体不适,但杨明健还是坚持打完比赛。最后,他的队伍无法出线。


Dota 2 The International Flickr Pix
须衡量人生抉择
比赛不久后,虎牙队在8月杪解散,而杨明健之后则辗转加盟数支战队。虽然受到业界看好成为新星,但杨明健一直没有打出好成绩。去年11月,他加入马来西亚战队Geek Fam,继续奋战。
面对不明朗的未来,杨明健给予自己最多两年的时间,尝试打职业电竞。
“我给自己一两年时间闯天下,如果不成就回去校园,一切都要在我20岁之前完成。”
同样的,亚当也认为,任何有意打职业电竞的年轻人,除非真的碰上黄金机会,否则不要把人生赌注押在电竞上。
“你应该自我衡量。除非机会跑上门来,否则你不应该把你的人生押注在打游戏。”
“好比我自己,我是因为获得Fnatic这个机会,才全心全力投入电竞。除非你获得机会,否则不应该为了打游戏而牺牲自己的人生。”
“这风险太高,可能你付出200%的努力,最后却一无所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