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观看所有入围2016国际足联普斯卡什奖的进球片段
视频取自 Messi The Alien
分享视频

视频取自 Messi The Alien
分享视频



图:迪斯尼
何笠方
学生,
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
在多数人的评价中,《海洋奇缘》(Disney’s Moana) 是不过不失的标准迪士尼公主电影,只是把舞台移到海上,以及女主角是来自南太平洋岛的原住民而已。这次影片中有两个人人都可注意到的特别手法:迪士尼公主没有与王子谈恋爱,因为影片压根儿没有王子这个角色;其次,公主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家园,协助她的半神人毛伊,是个不折不扣的“直男癌”。
这样的情节安排,仅仅是无创新地沿用了前作《勇敢传说》(Brave)、《冰雪奇缘》(Frozen)独立女性的人物设定吗?我们都知道,好莱坞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赚钱,还有较不明显的,宣扬某种生活方式。
在开篇的神话中,大地之母黛菲蒂孕育万物,半神人毛伊因为好大喜功,抢走大地之母的心之宝石,导致黑暗力量持续扩散,女主角莫娜的海岛即将遭到灭顶之灾。为了阻止部落小岛的灾难,莫娜踏上旅途把宝石归还给女神,海上冒险的过程中,她最终明白了自己要承担的使命。
整个故事就是标准迪斯尼套路,尽管叙事毫无意外,电影开场对性别再现是显而易见的:女性最高代表黛菲蒂的主要任务是繁衍,男性半神人毛伊如同远征的战士,靠掠夺以彰显力量。
西方一般将性别分成两种:强调先天性征的的生理性别(sexuality),如两性不同的生殖器官;以及后天形塑的社会性别(gender),比如男生性格大大咧咧,女生温柔婉约。摩土奴部落的男女分工反映了我们对性别差异(gender difference)的观念,展现出典范的阴柔特质与阳刚特质:采集椰子、编织、跳舞的多数是女性;制作削尖木棍、捕鱼的猎人则清一色是男性。
电影中,酋长父亲一直都在阻止女儿越过礁石,探索海洋。岛屿/家园是莫娜的牢笼,是压迫女性的父权体制之一。如同其他的女性公路电影一样,这也就决定了,莫娜必须要离家踏上旅途,才能自我发现,自我成长,成为寻路者。与父亲的强加安排不一样,祖母和母亲总是支持着莫娜寻找独立与自主的可能。
同许多男性电影中一样,男性毛伊的个性塑造较为扁平,他自恋自大,享受着人们对他的崇拜,努力符合社会所期待的男性理想样貌,是个硬汉。毛伊的男性气质通过武器镰刀的“类阳具形象”来隐喻,指涉了男性的权力。

图:迪斯尼
他不断与强者对决,以形塑自我认同。他把火、岛屿、阳光交给人类,只要完成了一些事情,毛伊的经历都会化为身上的刺青,就像是部落男性的一种成年礼仪式。毛伊之所以答应和莫娜踏上征途,是因为相信打败熔岩怪物德贾,就能重新获得“人类英雄”的美名与荣耀。
另一方面,半神人毛伊总是处于失去镰刀的焦虑之中,认为没有了镰刀的自己就不再是英雄毛伊,因为人们崇拜的是他的权力来源——镰刀,而非他本身。事实上父权体系中,男人也可以是受害者。他不敢示弱,剧组安排了毛伊身上的纹身小人充当旁白,说出逞强的隐情,来自于童年被抛弃的伤害。
冒险路上,战斗时在船上打鼓、画上银牙和黑眼妆的椰壳军团,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去年另一部父权极致社会下的女权主义电影《疯狂的麦克斯4:狂暴之路》(Mad Max4: Fury Road)。有趣的是,打败椰壳军团,是莫娜赢得半神人毛伊尊重的开始。
女性出走以后,对乌托邦的想象,常常需要遭受残酷的考验,《疯狂麦克斯》的Furiosa最终发现自己想寻找的家:绿地(The Green Place)并不存在。迪士尼对公主宽容得多,莫娜跨越障壁岛后,发现并没有什么需要打败的,熔岩怪物其实就是心被偷走而愤怒变形的黛菲蒂。
如果这是男性电影,高潮处必定上演最后一分钟救援:莫娜要趁毛伊奋力抵抗熔岩怪物德贾的有限时间内,把黛菲蒂之心放回原处,再倒回来打败德贾。男性要一直战胜强者,不然男性气质就会永远处在危机中,但女性没有这样的竞争焦虑。
和《驯龙高手》(How to Train Your Dragon)的男主角小嗝嗝不同,莫娜不用除掉巨龙的威胁,来获得继承父亲维京首领地位的资格。她所做的只是,把被男性夺走的、属于女性最宝贵的存在,归还给了女性。
紧要关头时,终究还是莫娜与毛伊合作,才完成救赎,重获新生。最终,毛伊的镰刀获得修复,岛屿恢复生机。大地之母继续孕育万物,完成生命传承;莫娜明白了自己身为酋长继任者的责任与使命,重启祖先的航海冒险,履行世代传承。(事实上,“莫娜”这个词在波利尼西亚语,就是“海洋”的意思。)

图:迪斯尼
女性可以领导众人航海,男性不需要权力与武器的力量来达成自我认同。不需受到不必要的约束,女性的解放,就是所有人的解放,女人自由了,男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。正如女性主义论者莫莉海斯柯(Molly Haskell)所说的:“无论在银幕上和银幕下,我们都只不过要有和男性一样多元丰富的选择罢了!”
尽管对抗父权、家庭作为牢笼的意象、归还与重生、女性的独立自主与解放,在性别流动的今天看来相当老套。但《海洋奇缘》反映了迪士尼在时代变迁影响下,为了取悦庞大的女孩消费者,迅速提升与普及的女性意识。《海洋奇缘》当然是一部公主电影,但是它是一部有着新女性形象的公主电影。


影院最近好戏不断,但若要选出能在大马各族群引起讨论并赞好的电影,相信赶在2016年结束前上映的宝莱坞电影《摔跤》(Dangal)会是其一。
UTV Motion Pictures
注意:扰流警报
《摔跤》能引起关注并非偶然。它是由大名鼎鼎的印度影帝阿米尔汗(Aamir Khan)担任制作人及主演,加上罕见的摔跤剧情,从2016年12月第3周开画至今,已在全球取得接近800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。
电影剧情按真人真事改编,讲述一名印度前摔跤国家冠军玛哈维尔(Mahavir Singh Phogat,阿米尔汗饰)训练他两名女儿成为摔跤手,进而在2010年德里共和联邦运动会上采金夺银的故事。
一些网民与媒体褒扬《摔跤》乃提倡性别平权之作,但综观整部电影的性别权力铺排,这个结论实有可议之处。

女儿成儿子替代品
电影伊始,玛哈维尔就希望妻子能生男,以圆自己无法参加国际摔跤赛,为国家夺金的梦想。然而,一连四胎女儿的残酷现实,令玛哈维尔心灰意冷。
惟一次偶然的机会,让玛哈维尔灵机一动,决定把梦想寄托于长女吉妲(Geeta Phogat)和次女芭比妲(Babita Phogat)。
他无视妻子的反对,不理街坊异样眼光,执意要将她们培训成顶尖摔跤手。
自此,尽管当时还是小学生,吉妲和芭比妲就开始接受地狱式训练,从早上5点就起床受训,之后再上学,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床,周而复始。
玛哈维尔为了有利训练,强迫她们放弃印度传统服装,改穿T恤短裤,更无视女儿泪流满面,狠心地剪掉他们的长发。
直观上,此举挑战印度传统性别角色,但吊诡的是,父亲的权力却无比扩张,两名女儿的主体反之被压缩至无形。

新旧父亲的异与同
虽然玛哈维尔个人意志的施展,无意间冲击了印度传统性别桎梏,使得其两个女儿得以离开“学做家务,等待嫁人”的印度传统女性的命运,这点无疑有进步意义。
而电影也“安排”了吉妲与芭比妲的一名14岁的“早婚”女同学,突出玛哈维尔的“新好男人”形象。
这名女同学的父母视她为“赔钱货”,硬把他嫁给一名老翁,以摆脱她这个包袱。女同学在婚礼上一脸愁苦,羡慕吉妲和芭比妲,有个为她们着想的好父亲,要栽培她们成为杰出的运动员。
只是,从旧式坏父亲到“新好父亲”,男性权威依然没有消减,玛哈维尔强迫两名女儿臣服于他为国夺金的意志,一切由他说了算,这种强悍作风跟“强迫女儿出嫁”没有太大差别,只是多了受现代社会接受的“良善”出发点。

否定女性成长自主
无论如何,女同学一席话令吉妲与芭比妲茅塞顿开,自此不再偷懒,勤奋训练,而吉妲也攀升全国冠军,进入国家体育学院,受训为国“出战”。
至此,玛哈维尔的“父亲”权力受到了挑战。这个挑战者不是别人,正是玛哈维尔自己的“好父亲”,那个他在兹念兹的“国家”。
摔跤队“国家”教练唾弃他教吉妲的“土炼钢”技能,在吉妲和众人面前,狠狠地摔破他的权威形象。
在两种男性权威冲撞下,吉妲却获得难得的自我成长空间,摆脱父亲的牢牢掌控,在少女情窦初开下探索新世界,蓄长发、血拼、涂指甲油、学习舞蹈、看电影等。
吉妲这种成长却最终发展为吉妲跟玛哈维尔之间的父女冲突,在一次回乡探亲时,吉妲更在摔跤场上一举把父亲打倒在沙地上。
不过,这种“弑父”行为不得祝福,电影剧情将之定性为“堕落”和“叛逆”,不得好下场,吉妲在国际赛事上连败不止。但在此同时,通过镜头交叉转换,电影凸显她妹妹芭比妲的“听话顺服”,在依循父亲指导下,连连胜利而来到国家体育学院。
这一败一胜的对比,突出“不听话女儿”与“听话女儿”的坏好下场。
最终,吉妲在赛事不断挫败后,听取妹妹的劝告,拨电话向玛哈维尔求援,回归“驯服女儿”的位置。

金牌换取父亲肯定
吉妲与芭比妲小时受训时,她们的母亲曾向玛哈维尔抱怨,担心女儿参加摔跤会导致她们嫁不出去。当时,玛哈维尔自信地放话,只要他成功,届时是女儿选男人,而非男人选她们。
在另一幕,国际金牌战前夕,玛哈维尔向女儿精神讲话,提醒吉妲的胜利将成为印度其他千千万万女性的楷模。
这些看似推崇女权的情节其实只是《摔跤》的旁支,而电影透过吉妲堂哥的男性视角,看叔叔如何达成“为国争金”心愿,恐怕才是真正主轴。在这种脉络下,吉妲与芭比妲反沦为男性荣耀的工具。
电影尾声,吉妲勇挫强大对手赢得金牌,惟她选择抛下教练和媒体,奔向玛哈维尔,领取“父亲”给予的荣耀封赏,一句“我以你为荣”。
而坐在荧幕前的你,是看到一名望女成凤的父亲,还是看见一名完成父亲心愿的女儿?《摔跤》到底是推崇性别平权,挑战印度根深蒂固的价值观,还是以国家荣耀来粉饰新形式的性别压迫?《摔跤》真的摔掉了“父亲”吗?

罗兴亚人是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族群,他们自称是古代阿拉伯商人的后代,住在缅甸西海岸的若开邦(前称阿拉干),不过亦有人说他们是从孟加拉移民而来。
缅甸在1948年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后,罗兴亚人受认可为缅甸公民,也曾经有投票权。
然而,缅甸军政府在1982年颁布新公民权法令,承认境内135个民族的身份,却剔除了罗兴亚人和其他五个民族。这导致80万名罗兴亚人顿时成为无国籍难民。
2013年,有130万罗兴亚人居住在若开邦,主要集中在北部靠近孟加拉的地区。
2014年,缅甸政府禁用“罗兴亚”一词,指称他们为“孟加拉人”。

若开邦佛教徒和罗兴亚人之间的冲突在英殖民期间(1824至1948年)就开始,当时英殖民者为了殖民地发展,鼓励孟加拉移民进入,也把土地租给他们耕种。这导致阿拉干佛教徒被迫离开原有土地。
当时,英国人直接统治缅甸佛教徒,但同时却允许罗兴亚人自治。在1942至1945年日据时期,英国人为罗兴亚人提供武器以对抗日本人。1942年,罗兴亚人与阿拉干人爆发冲突,据称双方死伤惨重。
阿拉干人认为,罗兴亚好战分子与英国殖民者共谋。
缅甸于1948年独立后,罗兴亚人即要求独立建国,但遭新政府反对。据称,一些罗兴亚人最终发动圣战,对付若开邦佛教徒和僧侣,也破坏佛教庙宇,以期建立穆斯林国家。
1962年的军事政变后,缅甸军政府开始镇压罗兴亚人,造成罗兴亚人大批出逃。

自军政府开始镇压,罗兴亚人数十年来皆四处逃难,其中最大批的逃难潮是在70年代,当时军政府强迫25万罗兴亚人逃至孟加拉。
种族冲突相继发生后,罗兴亚人也在90年代早期、2000年代初期和2012年前后被迫离开家园。
10月9日,在靠近孟加拉的三个边境站,有9名边防军遭杀害后,缅甸军队封锁若开邦北部地区。
缅甸政府说,袭击者是伊斯兰好战分子,因此开始搜索罗兴亚圣战士。
罗兴亚村落遭封锁后,对16万名罗兴亚人的人道救援无法送达。
有报道指,至少有86人死亡,过去9个星期以来不断有大肆逮捕、强暴和烧毁村落,造成10万人逃至孟加拉。
这令人联想起2012年若开邦的穆斯林和佛教徒骚乱事件,当时有200人死亡,15万人流离失所,大部分是罗兴亚人。


估计约有8万人,其中有5万4856人拥有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证件。罗兴亚人在马已至少有两个世代。
大马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宪章,因此并不承认难民身份。而在马的罗兴亚人必须生活,只好冒险非法打工,易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,也面对剥削。
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正规教育,仅能上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团体办的学校。而许多没有经济能力的难民,其孩子更无法接受教育。
大马也有罗兴亚协会,是个由罗兴亚人和联合国难民署发起的自救团体。

首相纳吉连同一些内阁成员参与了万人声援集会,政府也因罗兴亚镇压事件传召缅甸大使。
外交部长阿尼法试图和缅甸外交部长昂山舒吉见面,不过昂山拒绝与大马商谈罗兴亚课题。
大马应公众舆论而在这个月取消了两场和缅甸的足球友谊赛。
另外,政府计划允许300名罗兴亚难民在马工作。

纳吉参与集会前,缅甸已警告马来西亚,别干涉缅甸内政。
缅甸也事后传召大马驻缅大使,表达不满,并停止输送劳工至马来西亚。
缅甸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也批评,纳吉的行动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大马选举中拉票。
缅甸报章声称,有约100名示威者在仰光市区集会,抗议纳吉插手缅甸事务。
他们要求缅甸外交部和东盟国家,劝诫大马首相维护“东盟价值”。
昂山舒吉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缅甸大选中胜出,被视为写下缅甸民主新篇章。但她在罗兴亚课题上保持沉默,而遭受国际批评。
上周,她说缅甸政府有能力处理此事。她也要求国际社会助缅甸维持和平和稳定,并指责各界勿炒作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社群之间的憎恨。
报道称,昂山舒吉否认若开邦事件是“大屠杀”,也批评一些说罗兴亚人遭强暴、纵火和屠杀的指控是“外部捏造”。

67岁的她将半生都奉献给巴勒斯坦人,自己也更曾是无国籍难民

苏颖欣
助理编辑,《当今大马》
在战火无情的中东,尤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为历久而复杂。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下,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大举迁离家园,在异地成了难民。
67岁的洪瑞钗医生带着倦容,轻声说出坚定有力的字句。她穿起黑色的大衣显得身形更娇小,难以想象这位半生奉献给巴勒斯坦人的骨科医生,自己也曾是无国籍难民。

苏颖欣
助理编辑,《当今大马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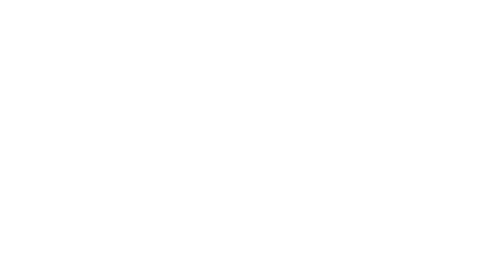

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《当今大马》的专访
战地医生洪瑞钗接受《当今大马》的专访
她10月底到吉隆坡出席著作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中译本的发布会,并在文运书坊和读者分享她的巴勒斯坦经验,事后接受《当今大马》专访。
在槟城出生、新加坡成长的洪瑞钗,是新加坡大学医学系毕业生。1977年,她新婚的人权律师丈夫丘甲祥遭新加坡政府通缉,当时丘甲祥已是著名异议分子,曾为被指发动暴动的工人辩护,绘制政治讽刺漫画。当逮捕的风声到来,他选择逃亡至伦敦。

洪瑞钗著作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
洪瑞钗著作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
警方随后找上洪瑞钗,彻夜盘问、迫使她签署招供书,要她劝丈夫回新受审。洪瑞钗签了字,飞往伦敦和丈夫聚首,两人从此展开流亡生活。“我丈夫完全不想知道我到底签了什么,他说,‘没关系,在酷刑下,人人都会签那些愚蠢的东西。’”
2014年,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《星国恋》遭新加坡政府以“威胁国安”为由禁映,却引起大批新加坡人租巴士过长堤到新山观看禁片。这部影片访问数名新加坡政治流亡者,包括前学运领袖、共产党员、人权律师等,而洪瑞钗也是受访者之一。
她在片中谈起两人的流亡生活,丘甲祥如何以诗歌怀念无法重返的家乡,并在2011年因病去世。洪瑞钗和丘甲祥于1984年在英国创办非政府组织“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”(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),不遗余力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援。

《星国恋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
《星国恋》由陈彬彬导演执导的纪录片
这个机构的起源,是由于洪瑞钗在1982年到黎巴嫩当医生志工时,见证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种种暴力。她更是萨布拉—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(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)的见证者和幸存者。
“当时,我不是英国公民,还拿着难民证件。英国当局未把我的名字列在幸存英国人的名单中,甲祥在伦敦非常惊慌。”
“他以为,我一定是被杀了。”
洪瑞钗和一些外国志工当时被以色列军队逮捕,所幸她的亚洲面孔让她得以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角力之间逃脱,幸存下来。
洪瑞钗是虔诚的基督徒,她说,自己曾“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”,因她的新加坡教会立场坚定。
“他们认为,以色列得以建国是上帝的旨意。他们认为,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苦痛,现在有了家园,我们必须支持。”
“我们也被教导,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,其他都是封建的阿拉伯王朝。”
1977年,洪瑞钗和丈夫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,就此在伦敦生活。某天,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,看见电视新闻画面出现被轰炸的场景——那是1982年的黎巴嫩。
新闻说,以色列入侵黎巴嫩,以摧毁流亡到黎巴嫩的“恐怖组织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(PLO)。
当时,她也相信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,但在跟进新闻后发现被杀害的不是所谓的巴解恐怖分子,而是像她一样的普通人、妇女和小孩。她开始和教会的朋友争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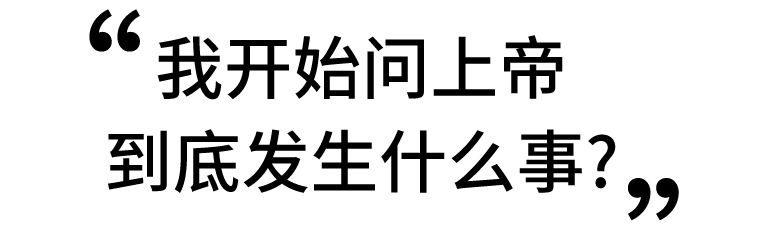
“这不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,这是破坏医院、学校、工厂的行动,造成无数人为了躲避轰炸而流离失所,成了难民。”
当时,有组织刚好在征求骨科医生到黎巴嫩。丘甲祥告诉她,“如果我是医生,我一定会去,可惜我不是。没人在征求律师。”

洪瑞钗最终和组织签了合约,从任职的医院离开,前往黎巴嫩。
“身为政治难民,要在英国重建我的医生事业是困难的。那时我已在其中一家最好的大学医院上班。”
“第一,你是有色人种,一个新加坡华人;第二,你是个女人。(有了稳定工作后)你不会选择就这样辞职离开。”
但她还是离职了。
1982年,洪瑞钗抵达贝鲁特,在加沙医院建立整形外科部门。当时,以色列已连续10周炮轰黎巴嫩,占领多个地区,而巴解组织终于在停火协议下答应撤退;由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也答应,将维护难民营老弱妇孺的安全。
“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。人们相信那些和平协议,因为他们真的要和平。”
她不知道,三个星期后,医院外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,会遭到大屠杀。坦克直接开入难民营将之封锁三天三夜,估计有3000人被杀。
这起事件的肇因和动机各方有诸多解释,一般相信是因黎巴嫩新当选的基督教长枪党总统巴希尔杰马耶(Bachir Gemayel)遇袭身亡,而巴勒斯坦民兵被认定是暗杀事件的凶手。
不少人也认为以色列是背后主谋,並以“搜捕剩余的巴解恐怖分子”为由,作为清洗难民营的合理借口,而多国维和部队也早已悄然撤军。
亲眼目睹难民营惨况的洪瑞钗,在手术室里没日没夜的开刀。她回忆,当自己在努力拯救数人的生命时,外头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。她不停追问:“为什么他们要怎么做?”
“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没办法自卫,他们没有武器,没有枪。”
“女人被强暴,头颅被砍,这是多残忍的屠杀。巴解组织已经撤退了,他们怎么还要对付这些妇女和小孩?”
原本只预计在黎巴嫩待两个月的洪瑞钗,最后决定留下。她把亲眼见到的战地状况快电给在伦敦的丈夫,让他把消息广布。
而她也开始接受采访,向世人披露真相,甚至带着第一手资料到耶路撒冷的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(The Kahan Commission of Inquiry)作证。
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在1989年出版,即记录了她的所见所闻。这本书在2015年和2016年再版,补充了最新的以巴资讯,中译本也終於在今年出版。
演讲中她分享许多照片,有在废墟中比起胜利手势的小孩,也有血肉模糊的受伤躯体,一些观众忍不住拭泪。
“巴勒斯坦人很美丽,至少我碰到的难民皆是如此,他们善良又文明。你很难在他们的家久坐,因为他们即使生存困难,只要他们有什么,他们都要给你。”
“我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自私感到羞愧,我们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分享;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么少,但却如此慷慨宽厚。”
见证了大屠杀后,洪瑞钗与丈夫在伦敦设立“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”组织,30余年来不断进出中东,协助巴勒斯坦人。
洪瑞钗在教学时,总提醒年轻医生:“你先是一个人,才是一名医生。”
“如果你忘了身为人的原则,如果你不为正义发声,不负起责任,那我们就能直接以机器人取代你。”
“要说动手术,机器人可能比你和我都做得好,但机器人不会爱。幸运的是,我们能选择对或错,作为专业医生,我们能做的事很多。”
2014年,洪瑞钗被以色列禁止入境,甚至被扣留,她和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命运似乎又再靠近了一些。他们心中皆有个回不去的“家”,一辈子成为异乡人。
离开新加坡已近40年,洪瑞钗在家的日子只有6天。那是2011年,新加坡政府特准她带丈夫丘甲祥的骨灰返新。丘甲祥因病去世,洪瑞钗来不及见上他最后一面。

之后,她再无法进入新加坡,就连今年3月她获选列入新加坡女性名人堂,也无法获特准入境。
洪瑞钗的公民身份颇复杂,她和丘甲祥1977年前往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时,原本能在5年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,但他们皆坚持保留新加坡身份。
即便在80年代她频密往返中东,却仍然只持有政治庇护者的旅行证件。
“在机场,一定会被移民官员拉到一旁盘问,有时半小时,有时两三小时。随行的朋友都很着急。”
1990年,洪瑞钗母亲去世,她向新加坡申请入境却不获准。而他们也因东盟之间有相关协议,无法入境马来西亚。
终于,她告诉丘甲祥:“就吞下我们的自尊心吧,申请英国护照,至少我们能到新山和家人见面。”
自此,她更能自由在中东国家行动,因英国政府同意给她两本护照,一本入境阿拉伯国家,一本入境以色列,以免遇到困难。不过,她最终仍遭以色列列入黑名单,遣返回英国。
洪瑞釵带着丈夫骨灰回新后,新加坡政府即要求她放弃英国国籍,否则无法保留新加坡国籍,但她坚持不放弃新加坡身份。
“他们可以夺走我的公民权,但我不会自动放弃新加坡公民权。”
“我被迫离开新加坡,那是不公平的,内安法令是不公的法律,是英国殖民者统治新马时的邪恶发明。”
而她虽然愿意放弃英国国籍,但申请过程繁琐,而这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在英国的事业,在新加坡重新开始,她也可能无法继续援助巴勒斯坦人,因此她并没选择这么做。
“回到新加坡后,他们可能不给我护照,也不会给我两本护照,那我怎么去帮助巴勒斯坦人?这不只是我一人的事,我有责任。这是我无法放弃英国国籍的原因。”
洪瑞钗的母语是华语,但离家40年后,她已经不太能说华语。新加坡仍是妳的家吗?我问她。“我家已经因兴建地铁而毁了”,她笑说。
“我仍是新加坡人,公民权只是一张纸。”
“其实,帮助巴勒斯坦人,也是我身为新加坡人的责任。”
她说,新加坡公民在学校、国庆等典礼中必须宣誓“国家信约”,里头提及国人不分种族、语言、宗教,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。
“我认真实践(这项信约)。写下信约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,但作为宣读信约的新加坡人,我是认真的。”